
达拉书院 > > 宋时明月照清欢(一种茶筅)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宋时明月照清欢热门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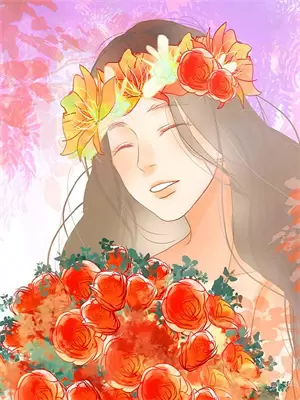
言情小说连载
书名:《宋时明月照清欢》本书主角有一种茶筅,作品情感生动,剧情紧凑,出自作者“华无华”之手,本书精彩章节:剧情人物是茶筅,一种,冰冷的古代小说《宋时明月照清欢》,由网络作家“华无华”所著,情节扣人心弦,本站TXT全本,欢迎阅读!本书共计14162字,1章节,更新日期为2025-07-05 01:10:59。目前在本网 sjyso.com上完结。小说详情介绍:宋时明月照清欢
主角:一种,茶筅 更新:2025-07-05 02:12:25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建州的风,裹着南剑州山峦深处特有的草木清冽气息,吹过晏家小院低矮的土墙。
院中那株老枇杷树,阔大的叶子在风里翻卷,筛下碎金般的光斑,跳跃在阿爹佝偻的脊背上。
他正蹲在青石垒砌的茶灶前,神情专注得像在雕琢稀世珍宝。一只素面粗陶风炉,
炉膛里松炭烧得正旺,跳跃着橙红的火苗。炉上架着的铁釜中,
山泉水已发出细微的、蟹眼似的轻响。阿爹布满粗茧和老茧的手,稳稳提起釜,
将滚水注入旁边温着的兔毫盏里。水汽氤氲升腾,模糊了他沟壑纵横的脸,
却清晰映出那双眼睛里近乎虔诚的光。“清殊,来。”他声音低沉沙哑,
带着山风磨砺的粗粝感。我应声过去,跪坐在蒲团上,递上早已备好的青竹茶筅。
阿爹接过去,没看我,目光凝在盏中。他右手执壶,
左手指尖捏起一小撮碾得极细、如尘如雾的建茶“龙团胜雪”茶粉,雪沫似的,
无声撒入温热的盏底。“看好了,”他喉头滚动,每个字都像从肺腑深处抠出来,
带着血气和山岩的沉重,“建州这山山水水养出的茶脉,是晏家的命!一丝一缕,
都连着祖宗魂魄,连着往后子孙的活路!”滚烫的初沸水如银线泻落,
精准地冲击在盏底茶粉上。阿爹手腕一振,茶筅闪电般探入,手腕带动小臂,
以某种奇异而圆融的力道搅动起来。初时无声,只有茶粉与水交融的细密声响。渐渐地,
那盏中混沌的茶汤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开始旋转、聚合。茶筅在他手中发出“刷刷”的轻啸,
越来越快,越来越急,带着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韵律。茶沫,一层层、一圈圈地涌现出来。
先是细碎如鱼眼,继而紧密如蟹沫,最终竟堆叠、凝结,如同初冬最细密的新雪,
洁白得耀眼,丰盈得几乎要溢出盏沿。那雪沫表面,竟隐隐泛着一层珍珠般柔和的虹彩,
在午后穿透枇杷叶的光线下,流转着无法言喻的光华。茶香,不再是清幽的草木气息,
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凝练到极致、几乎有了实体的馥郁,霸道地充盈了整个小院,
冲散了松炭的烟火气,压下了草木的清新。我看着那盏中凝固的雪浪,呼吸都屏住了。
这哪里是茶?分明是阿爹用骨血魂魄,在盏中祭出的一座雪山!“记住了,清殊,
”阿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更多的却是磐石般的坚定,“七汤点茶,
汤瓶注水如悬河落九天,茶筅击拂如惊涛卷霜雪。要快,要稳,要狠!心无旁骛,神凝一点!
这茶沫,要白如雪,厚如云,聚而不散,咬盏不消!这才配得上我们晏家守护的茶脉!
”他小心地将兔毫盏捧到我面前。那雪沫果然紧紧“咬”着盏壁,凝立如峰,久久不塌。
我伸出指尖,极轻极轻地触碰了一下那雪白的顶峰,冰凉,柔韧,带着一股沁入骨髓的茶韵。
“阿爹,”我仰起头,望着他因常年烟熏火燎而显得格外深刻的皱纹,
“它像……像月亮掉进盏里了。”阿爹布满风霜的脸上,
终于绽开一丝极淡、却深及眼底的笑意。他粗糙的大手落在我发顶,轻轻揉了揉。“傻丫头,
是明月照清欢啊。”他抬眼望向院外起伏的、墨绿色的茶山轮廓,目光悠远,“守住这茶脉,
守住这盏里的明月光,日子再苦,心里头就有那么点清亮,有口清欢可尝。
”那是我最后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阿爹眼中那捧“明月光”。建州府衙前的广场,
早已人声鼎沸,水泄不通。空气里弥漫着蒸腾的水汽、汗味、劣质脂粉香,
还有无数种茶叶混合的气息,发酵出一种令人窒息的躁动。一年一度的“茗战”,
是建州茶人最大的盛事,更是决定各家茶场来年兴衰荣辱的生死场。阿爹脊背挺得笔直,
像一株扎根在风口的古松。他穿着浆洗得发白、却一丝褶皱也无的靛蓝布衫,
独自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一角。身边那些或锦袍玉带、或绸缎加身的茶商大户们,
投来的目光混杂着审视、戒备,甚至隐隐的敌意。晏家茶场太小了,
小得像山岩缝里倔强钻出的一棵野茶树,
却偏偏年年都结出让所有大茶商都坐立不安的“金叶子”。我挤在人群最前面,
心揪得紧紧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感觉不到疼。目光死死锁在高台中央那张紫檀长案上。
案上摆放着数十只形态各异的茶盏,每一只都代表着一方势力,一场无声的厮杀。评判开始。
府衙请来的几位须发皆白、神态倨傲的老茶博士,捻着胡须,慢条斯理地踱步。
他们或俯身细嗅茶香,或眯眼观察茶沫的色泽、形态和“咬盏”的程度,
间或低声交换几句意见,引得台下相关的人一阵阵骚动。每一次有人被淘汰,
便有小吏面无表情地将那盏茶连盏带汤泼洒下高台,引来一片惋惜或幸灾乐祸的哗然。
案上的茶盏越来越少,气氛也越来越凝重,空气仿佛凝固的油脂,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胸口。
终于,紫檀长案上,只剩下两只茶盏遥遥相对。一只,
是胎骨厚重、釉色深沉如夜的黑釉建盏,盏口阔大,正是阿爹带来的那只,
盏中茶沫洁白如雪,凝厚如云,稳稳地“咬”着盏壁,
在午后的阳光下流转着珍珠般温润的毫光。另一只,
是胎薄如纸、釉色青翠欲滴的越窑秘色瓷斗笠盏,盏型秀雅,
属于建州最大的茶商——万记茶行的东家万正奎。他站在阿爹对面,
一身簇新的宝蓝团花绸袍,面皮白净,保养得宜,一双细长的眼睛半眯着,
嘴角噙着一丝志在必得的微笑,目光偶尔扫过阿爹,那眼神深处,却像淬了毒的冰针,
带着毫不掩饰的阴冷和志在必得的贪婪。几位老茶博士围着这两只盏,
低声商议的时间格外漫长。台下的喧嚣也渐渐平息,
无数双眼睛灼灼地盯着那两张决定命运的茶案。我的心跳得像要撞碎肋骨。终于,
为首那位最年长的茶博士,颤巍巍地直起身,清了清嗓子。广场上瞬间落针可闻。
“经我等反复品鉴,斟酌再三……”老博士的声音带着暮气的沙哑,却清晰地传遍全场,
“晏氏茶场所贡之‘龙团胜雪’,其沫……白胜新雪,厚若凝脂,聚而不散,咬盏逾刻不消。
其香……凝练醇厚,沁人肺腑,隐有山岚之气,深得建茶‘骨鲠’之韵!”他顿了顿,
目光扫过台下屏息的人群,
最后落在阿爹那张因常年辛劳而显得格外沧桑、此刻却绷得如岩石般坚硬的脸上。
“故此一局,茗战魁首——晏氏茶场!”“轰!”巨大的声浪瞬间爆发开来,
淹没了老博士后面的话。有欢呼,有惊叹,更多的是难以置信的抽气和嗡嗡的议论。
万正奎脸上的笑容瞬间冻住,随即扭曲,那层虚伪的温和被彻底撕碎,
露出底下铁青的底色和眼中翻涌的毒火。他死死盯着阿爹,那眼神,像淬了剧毒的匕首,
恨不得立刻将阿爹钉死在当场。阿爹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随即挺得更直。
他对着评判席方向,深深一揖,动作缓慢而沉重,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当他直起身时,
我看到他额角有汗珠滚落,砸在脚下的木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他脸上没有狂喜,
只有一种近乎悲怆的释然和深不见底的疲惫。几个小吏费力地抬着一块沉重的木匾走上高台。
匾额用上好楠木制成,边缘雕着缠枝莲纹,
中间四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刺目地闪耀着——茗战魁首。万正奎拂袖而去,
宝蓝绸袍在拥挤的人潮中像一片阴冷的云,迅速飘远,只留下一道冰锥般的视线,
狠狠剜过阿爹的背影。人群簇拥着阿爹,推搡着,喧闹着,
像潮水般涌向晏家那间简陋的茶寮。阿爹被众人拱卫在中间,步履有些踉跄,
脸上挤出的笑容僵硬而勉强。那块沉重的金匾被两个壮汉抬着,走在最前面,金光闪闪,
晃得人眼花。我落在最后,心却沉得像坠了块冰冷的石头,那金匾的光芒非但没有带来暖意,
反而像寒冰折射出的冷光,冻得我指尖发麻。万正奎离去时那淬毒的眼神,
像一条冰冷的毒蛇,死死缠住了我的心脏。“清殊!愣着干啥?快回家!
你阿爹今儿可是给咱晏家挣了大脸面了!”隔壁陈婶的大嗓门带着兴奋的颤抖,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不由分说地把我往前拽。小小的茶寮里挤满了人,
笑语喧哗几乎要掀翻茅草屋顶。粗瓷碗里倒满了浑浊的米酒,
劣质的花生米和炒豆子撒了一地。阿爹被按在唯一一张还算完好的竹椅上,
那块金匾就靠在他身后的土墙上,金粉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刺眼。“老晏!厉害啊!
万记都被你踩下去了!” “晏老哥,往后你家这‘龙团胜雪’,可得给我们匀点啊!
” “魁首!这可是真金白银的招牌啊!晏老哥,发达了可别忘了乡亲!”阿爹端着粗瓷碗,
勉强应和着。他脸上挂着笑,那笑容却像一张僵硬的面具,
浮在深深的疲惫和某种难以言喻的忧惧之上。他的目光越过喧闹的人群,落在我身上,
那眼神里盛满了复杂难言的情绪——有欣慰,有嘱托,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沉重。
他嘴唇无声地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就在这时,
茶寮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被猛地推开,撞在土墙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喧闹声戛然而止。
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男人。打头的是个精壮汉子,穿着半旧的皂色短打,腰间鼓鼓囊囊,
眼神凶悍,像刚出笼的斗犬。他身后跟着个瘦高的中年人,面色蜡黄,眼珠浑浊,
穿着绸布长衫,却皱巴巴的沾着油渍。两人身上都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戾气和浓重的酒气。
“哪个是晏老头?”精壮汉子粗声粗气地问,目光像刀子一样在众人脸上扫过,
最后钉在阿爹身上。茶寮里瞬间安静得可怕,刚才还闹哄哄的乡亲们,
此刻都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眼神躲闪。陈婶抓着我的手猛地收紧,指甲掐进了我的肉里。
阿爹慢慢放下手中的粗瓷碗,缓缓站起身。他的背脊依旧挺直,
但脸色在昏暗中显得更加灰败。“鄙人便是。不知二位寻我何事?”“何事?
”那精壮汉子嗤笑一声,大步走到阿爹面前,一股浓烈的酒臭扑面而来。“装什么糊涂?
你晏家茶场那三亩坡地,挡了我们东家新开的矿道!识相的,赶紧把地契拿来!
我们东家心善,赏你几贯铜钱,够你买口薄棺材了!”“放屁!”阿爹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破釜沉舟般的嘶哑,“那是我晏家祖传的茶山!地契在官府备了案,白纸黑字!
你们想强占?”“强占?”那瘦高个慢悠悠踱上前,浑浊的眼珠里闪着毒蛇般的光,
“晏老头,话别说得那么难听。你那破茶山值几个钱?挡了矿道,误了东家的大事,
把你全家填进去都赔不起!地契?”他干笑两声,声音像砂纸摩擦,
“谁知道你那地契是不是真的?说不定是伪造的呢?”他猛地一拍桌子,
震得碗碟乱跳:“少废话!今日这地契,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话音未落,
那精壮汉子一步上前,蒲扇般的大手就朝阿爹胸口衣襟抓去!“滚开!”阿爹怒吼一声,
积压了一整日的悲愤和屈辱瞬间爆发。他猛地抄起身旁一把沉重的竹椅,
用尽全身力气抡了过去!动作带着茶农常年劳作练就的狠劲,又快又猛!“砰!”一声闷响,
竹椅狠狠砸在精壮汉子的肩膀上。那汉子猝不及防,痛吼一声,踉跄着退了两步,
撞翻了旁边的桌子,杯盘碗盏稀里哗啦碎了一地。“反了你了!老东西!
”瘦高个眼中凶光毕露,厉声喝道,“给我往死里打!”精壮汉子红了眼,揉着肩膀,
像被激怒的疯牛,低吼着再次扑上!瘦高个也从腰间摸出一把短匕,寒光一闪,
阴狠地刺向阿爹肋下!小小的茶寮瞬间成了修罗场!桌椅翻倒,碗碟碎裂,
酒水混着花生米泼洒一地。乡亲们尖叫着,哭喊着,连滚带爬地往门外挤,生怕被殃及。
阿爹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挥舞着断裂的竹椅腿,
奋力抵挡着两个恶徒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他毕竟年老体衰,
又刚刚经历了一场耗尽心神的大比,动作越来越滞涩。那精壮汉子一拳狠狠捣在他腹部,
阿爹闷哼一声,痛苦地弯下腰。就在这一瞬,瘦高个眼中寒光一闪,那柄淬毒的短匕,
无声无息地,带着最阴险的轨迹,猛地刺向阿爹的后心!“阿爹——!!!
”我撕心裂肺的尖叫冲破喉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混乱中,
不知是谁撞倒了墙边那盏昏暗的油灯。“哐当!”灯盏摔碎在地上,
微弱的火苗猛地舔舐上泼洒开的灯油和茅草墙壁!“呼——!”火焰如同被唤醒的赤色毒蛇,
瞬间窜起,贪婪地吞噬着干燥的茅草和木梁!浓烟滚滚,带着刺鼻的焦糊味,
刹那间弥漫了整个狭小的空间!火光跳跃,将正在缠斗的三人扭曲成疯狂舞动的鬼影。
“走水啦!快跑啊!”门外传来惊惶的哭喊。混乱中,
我只看到瘦高个那张蜡黄的脸在火光和浓烟中一闪而过,
嘴角似乎勾起一个残忍而快意的弧度。随即,他和那精壮汉子如同鬼魅般,迅速抽身,
撞开混乱逃命的人群,消失在门外浓重的夜色里。“阿爹!阿爹!”我哭喊着,
不顾一切地要冲进那吞噬一切的火焰。“清殊!不能进去啊!”陈婶死死抱住我的腰,
哭得声嘶力竭,“火太大了!没用了!没用了啊!”熊熊烈火像一张巨大的、狞笑的魔口,
彻底吞没了那个佝偻着倒下的身影,吞没了那块刚刚挂上墙、金漆未干的“茗战魁首”匾额。
木匾在火焰中扭曲、变形,发出噼啪的爆裂声,刺目的金字迅速被浓烟和火舌舔舐、吞噬,
化为灰烬。滚烫的气浪扑面而来,带着阿爹残留的气息和血肉焦糊的恐怖味道。我眼前一黑,
巨大的悲恸和绝望像冰冷的潮水灭顶而来。整个世界在疯狂旋转,
火光、浓烟、哭喊、碎裂声……一切都扭曲成破碎的漩涡,最终归于一片死寂的黑暗。
……冷。刺骨的寒冷,像无数根冰针,扎透破旧单薄的衣衫,钻进骨头缝里。
我蜷缩在晏家茶场后山那个废弃的、仅容一人藏身的石砌炭窑里。
窑口用枯枝败叶小心地遮掩着,只留下一条狭窄的缝隙,透进外面惨淡的月光和凛冽的山风。
三天了。那场大火之后,万正奎的人像嗅到血腥味的豺狼,
在废墟和整个建州城疯狂地搜寻我,还有那块据说藏着晏家茶脉最大秘密的玉玦。是陈婶,
趁着夜色,用破麻袋把我裹起来,像拖一袋发霉的米粮,偷偷塞进了进山送炭的牛车夹层里,
才险险逃出了城。阿爹……阿爹没了。家没了。茶寮成了焦黑的断壁残垣,
连同那块带来灾祸的金匾,一起化作了灰烬。只有这深山里,晏家最后的三亩茶坡,
在寒冷的夜风里,沉默地伫立着。它们是我仅剩的命脉,是阿爹用命护住的根。
玉玦紧贴在心口,冰冷的触感却带来一丝奇异的暖流。这是一块半个掌心大小的古玉,
色泽温润如羊脂,形制古朴,边缘有云雷纹,中间镂雕着一个繁复的、类似茶芽的古老符号。
阿爹弥留之际,用尽最后力气塞进我怀里的。他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嘴唇翕动,
却发不出声音,只有口型在说:“茶脉……护住……玉……钥……”玉是钥匙?
开启什么的钥匙?茶脉的秘密?我茫然地摩挲着冰冷的玉玦,指尖划过那些繁复的纹路,
只觉得沉重如山。夜枭凄厉的啼叫在寂静的山林间回荡,更添几分阴森。远处,
似乎隐隐传来几声模糊的犬吠和人语。我的心猛地一缩,身体瞬间绷紧,
像一张拉到极限的弓。是搜寻的人!他们找到附近了!不能再等了!这深山也非久留之地。
万正奎的势力盘踞建州,只手遮天,我留在这里,迟早会被发现。玉玦的秘密,
晏家茶脉的生机……唯一的希望,似乎只剩下那遥远得如同传说的汴京城。
听说那里汇聚天下奇珍,也有最顶级的茶行,
或许……或许那里有能压过万记、能为阿爹讨回公道的路?念头一起,
如同野草在绝境中疯长。去汴京!必须去汴京!我咬紧牙关,将冰冷的玉玦更深地按在心口,
仿佛要从那冰冷的石头里汲取最后一丝支撑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寒意更重了,
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我抱紧双膝,将脸深深埋进臂弯里,只露出一双眼睛,
死死盯着缝隙外那片被月光照得惨白的山路。恐惧像冰冷的毒蛇缠绕着心脏,但更深处,
一股混合着悲愤和孤注一掷的火焰,正艰难地燃烧起来。活下去。护住茶脉。去汴京。
……三年后,汴京。初秋的夜风已带着明显的凉意,穿过御街两侧鳞次栉比的楼阁飞檐,
卷起地上零星的落叶。樊楼那高耸入云的彩楼欢门依旧流光溢彩,
丝竹管弦与行酒令的喧闹声浪隐隐传来,混合着脂粉香和酒气,织成一张巨大而奢靡的网,
笼罩着这座不夜之城。我低着头,脚步匆匆,尽量将自己缩在街道投下的阴影里。
身上的粗布襦裙洗得发白,袖口和裙摆都磨出了毛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粗布包裹,
里面是我视若性命的宝贝——阿爹留下的那套点茶器具:一个胎骨厚重的旧建盏,
边缘有一道细微的冰裂纹;一个形制古朴、口沿微缺的铜茶瓶;还有那支跟随阿爹多年,
竹节已被摩挲得无比光滑的茶筅。白日里,我在城西一家小茶肆后厨帮工,
清洗堆积如山的杯盏碗碟,双手长时间浸泡在碱水里,早已红肿开裂。
此刻正赶回赁居的陋巷小屋——一间低矮、终年弥漫着霉味和隔壁炊烟气的耳房。
刚拐进巷口,一股浓烈的劣酒气混杂着呕吐物的酸腐味扑面而来。昏暗的光线下,
一个肥胖的身影堵在狭窄的巷道中央,正是茶肆的管事刘二。他喝得醉醺醺,满面油光,
敞着怀,露出里面脏污的汗衫。“哟,这不是我们晏娘子吗?”刘二打了个响亮的酒嗝,
浑浊的眼睛在我身上滴溜溜地转,带着毫不掩饰的下流,“天儿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夜路,
多……多不安全啊!”他摇晃着肥硕的身体,故意朝我这边挤过来,
一只油腻腻的胖手就朝我胳膊上抓来。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我猛地侧身躲开,
指甲深深掐进怀里的粗布包裹,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和恐惧。“刘管事,请让让路。
”声音干涩紧绷。“让路?”刘二嘿嘿笑着,又逼近一步,酒气喷在我脸上,“急什么?
陪哥哥我说说话嘛!听说你以前也是茶户家的小姐?啧啧,落到这步田地,
怪可怜的……不如……”他另一只手竟直接朝我怀里摸来!“滚开!
”积压了三年的屈辱和愤怒在这一刻轰然爆发!我几乎是本能地,用尽全力狠狠撞开他!
“哎哟!”刘二没料到我会反抗,猝不及防被撞得一个趔趄,后背重重撞在湿冷的砖墙上,
痛得龇牙咧嘴。“小贱人!给脸不要脸!”他恼羞成怒,骂骂咧咧地站稳,脸上肥肉抖动,
眼中凶光毕露,抡起蒲扇般的巴掌就朝我脸上扇来!劲风扑面!我下意识闭上眼,
绝望地抱紧怀里的包裹。预期的剧痛并未落下。一道沉稳的男声在巷口响起,不高,
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瞬间冻结了巷子里污浊的空气。“住手。
”刘二的巴掌硬生生停在半空,离我的脸颊不过寸许。他脸上的凶横瞬间僵住,
转为一种谄媚又惊惧的惶恐,猛地扭头看向巷口。我也睁开眼,循声望去。
巷口停着一辆青幔马车,形制并不华丽,却透着一种低调的厚重感。车前挂着一盏素纱灯笼,
昏黄的光晕下,站着一个年轻男子。他身形颀长,穿着月白色的圆领襕衫,
外罩一件同色系的半臂,腰间束着玉带,通身无多余佩饰,只在夜色里显出一种清贵的疏离。
灯光勾勒出他侧脸的轮廓,鼻梁高挺,下颌线条清晰。他并未看刘二,
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身上。那目光并非审视,也非怜悯,更像是在看一件寻常之物,
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光天化日,御街之侧,强辱弱女,”男子的声音依旧平淡无波,
听不出情绪,“大宋律例,视同劫盗。你是想尝尝开封府的杀威棒,
还是想去沙门岛宋代流放重犯之地走一遭?”刘二脸上的肥肉剧烈地抽搐着,
酒意瞬间吓醒了大半。“大、大人!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就是……就是喝多了,
跟晏娘子开、开个玩笑!”他点头哈腰,语无伦次,额头上瞬间渗出冷汗。“玩笑?
”男子唇角似乎极细微地牵动了一下,那弧度冰冷,“滚。”一个字,轻飘飘的,
却像带着千钧之力。刘二如蒙大赦,再不敢看我一眼,连滚爬爬、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巷子,
肥胖的身影消失在御街的灯火阑珊处。狭窄的陋巷里,只剩下我,
和那个站在昏暗光影里的陌生男子。夜风穿过巷子,卷起地上的尘土和落叶,
发出呜咽般的声响。怀里的粗布包裹被我抱得死紧,粗糙的布料磨蹭着开裂红肿的手心,
带来一阵阵钝痛。我低着头,不敢看他。方才的愤怒和恐惧尚未完全平息,
身体还在微微颤抖。巷子太窄,他站在那里,挡住了唯一的去路,
网友评论
资讯推荐
最新评论